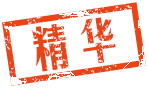|
2018年3月的某個周一晚上,湖南衛視做了一期胡歌特輯,在如同時光一樣緩緩流逝的畫面背后,謝娜用煽情的嗓音吟誦了那句催淚彈的旁白:”37歲的胡歌就坐在那里,深情的目光望過去,滿眼都是自己22歲的影子。” 我在電視前面泣不成聲,一邊哭一邊翻出柜頂落滿灰塵的舊胡歌壁畫,當場緬懷了曾經摯愛的明星,我撫摸著那些泛黃的畫報,思緒翻騰,胡茬唏噓,矯情地覺得自己正在用盡力氣祭奠即將逝去的青春。如果有人當場指出我的舉止有點中二,我一定會沖他大吼:“沒到深情時你特么就不會懂!” 其實回頭想想,那時候我還算年輕,遠不到祭奠青春的年紀。而轉眼間,將至的3月誕生日,27歲的生日就已經真的撲面而來了。 而我從來沒有留意到它會來得如此之快,如此令人猝不及防。 于是在這樣的夜晚,當我把疲憊的身體拋到床上,聽到窗外這夜晚的農村不時傳來青蛙蛙鳴的聲音,夜里喝掉的那杯茶在不停地鞭策著我的腦細胞在回溝里來回奔走。而只要閉上眼睛,就真的滿眼都是自己22歲影子。 22歲的時候我正在大學讀書,不到120斤,有一個女朋友現在的老婆和一幫狐朋狗友,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,下午去哪里看女孩,吃完晚飯回宿舍打麻將,我把頭發染成白色,穿寬大及膝的罩衫和垮褲,帶著“自己很帥”的錯覺搖擺著走過每個用怪異目光打量我的女生,周末在教學樓大廳和一群自戀癥患者一照鏡子看自己,22歲的我活在當下,憧憬未來,熄燈后和室友一起許愿說35歲前要實現財務自由,可實際上從來沒有考慮過明天該干嘛,以后做什么,買不起房子要怎么辦。未來,對于當時的我來說,還罩著重云密霧,那背后有無限的可能,我根本無法想象對面究竟會是一面山墻還是一條歧路。 畢業后我跟現在老婆東奔西走,狐朋狗友散落祖國各地,逐漸都不再聯系。體重逐漸上漲,快要飆升到140斤。每天朝八點半晚六,早已不玩網絡游戲,吃完晚飯經常刷夜看盤,頭發越來越少,胡子越長越多。學會規規矩矩走路,在電梯里低頭不發一言。想的最多的念頭再也不是“我很帥”,而是“我沒有做錯什么吧”。每個周末去單位加班然后不忘曬朋友圈。25歲的我活在圍城里,工作間歇和同事討論什么時候買一輛車,能不能買房,未來似乎清晰可辨,又似乎無可期待。 我驚奇地發現,27歲和22歲的自己已經幾乎沒有任何交集。五年過去,我變成了一個完完全全不同的人,仿佛不是從五年前的那個我一路老過來的一樣。就像我在左耳上打過的那個耳洞,它早已經完全長勻實了,就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。 三十而立,當如脊梁,不僅可以挺而為人,而且能夠撐起一方天地。以此標準反觀自己,二十有七而一事無成,簡直愧不能言。 聊聊事業吧。曾經以為牢不可破的理想早已羞于啟齒,已經失去的交易員身份也難以靠情懷自慰。風雨飄搖中的戰友們紛紛自省“我們還能期待些什么”,無可奈何的小伙伴只好自嘲“沒有什么可以失去了”。喝不下雞湯又看不慣悼詞,眼望著一批同齡人轉身離去而另一批早早躺下準備裝死,想說點什么,但連自己內心的忐忑不安都擺不平,又拿什么去勸慰別人的玩世不恭。立志為之奮斗的事業淪為一份工作,剩下的便是掰著手指就可以數得出的年頭。 那說說生活呢。全世界都在漲價而只有自己和工資單保持恒定,實在挺不直腰桿說要做家庭的頂梁柱。父母在我眼前老去,白發愈長而病痛漸多,兒子潼潼漸漸會吖吖而語,但暗自心痛之外也只能裝作視而不見,有如整個世界大廈將傾而無力去扶。曾經立誓要讓愛我的人愛得其所,如今卻使她囿于柴米油鹽、瑣事爭端,有心而無能許下任何一個宏大或昂貴的愿望,有如心愛之物掩埋于塵土而無力去拂。每個人的生活都打著一個個死結,大家都在埋頭去解,我又憑什么仰望星空? 也許再過五年,當32歲的我閉上雙眼,會都是自己27歲的影子。也許今天的迷惘就像22歲時的虛妄,一樣會成為明天笑談時的佐料。也許所有的結都會迎刃而解,也許更多的結會越纏越深。也許冷卻的熱血會在某一日浴火沸騰,也許頑固的情懷又真的是一種不治之癥。 再漂亮的青春紋身,終究有一天會變成皺紋。但不管怎樣,今天都是余生中最年輕的一天,依然可以擁有最多的可能。 一個忽然意識到韶華老去的雙魚座糾結癥患者寫給自己27歲生日的胡言亂語,也寫給他深愛過和深愛著的一切。給已白的頭發和逝去的青春。給共同打發過青春的好友和已經記不清楚的臉。給不知從哪里長出來的50斤肥肉。給所有曾經真誠或者昧著良心夸我帥的姑娘。給宏大的事業、渺小的生活,以及你們許給我的期待 生日快樂。給而立未立的自己,給未來期許的將來的世界,給一直默默奮斗任然一事無成的自己。
|